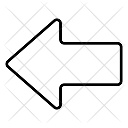 第十一讲
第十一讲
达摩的理入行入
二祖安心
四祖与各宗派
五祖的时代
六祖的时代
即心是佛的流弊
小释迦仰山
临济四料简
我们的课程已进入第五个礼拜的第二次了,实际修证的资料,因时间的关系,无法在这里作仔细研究,要大家自己去研究,光听而不研究是没有用的。
我们开始所讲的,是关于学佛见地方面,后来偏重于修证做功夫的事相。特别要注意的,是十念法中,修出入息的方法。这个修出入息的方法,因个人生理、心理的差异,而有所不同。佛说的念安般是大原则,当然每一句话,内容都很复杂,若能修好,绝对能做到健康长寿。若做不到,则是因为不得法,或者没有恒心。有了初步的修持,再进一步得定,发智慧、得神通,也都绝对能做到。至于详细的方法,当然不简单,密宗的修气、修脉、修明点、修拙火四部,都是修安般法门发展出来的。
先不谈悟道成佛,光说修养功夫,应参考孟子的养气原则,还有吕纯阳的《百字铭》:“养气忘言守,降心为不为”也非常重要。吕纯阳是道家,也学禅,他在《百字铭》中,把修证的事相,尤其炼出入息成就的步骤,都包括在内了,很值得研究。当然细则很多,非依明师不可,没有过来人指导,会走很多冤枉路,如由有经验的人点一句,则事半功倍。
前面所有关于修持法门的讨论,都属于四加行的范围。修气的法门与心物的关系,因时间不够,暂时摆下不谈。
现在再介绍中国学佛的修持路子。
前几次谈到自东汉以后,到了南北朝、隋唐之间,修行有成就的人很多,尤其是隋唐以前,走的都是小乘的修持法门。后世有一个毛病,一听小乘就看不起,这也是颠倒因果。我也再三地说,学大乘没有小乘基础,根本就不必谈,等于小学基础没打好,怎么读大学呢!唐宋以后,禅宗兴盛了,证果的人却越来越少,而说理的越来越多,直到现在,都是如此。一般人动辄参话头、参公案,或者观心、默照,统统叫它是禅,这都是笑话,都在颠倒因果。
东晋时代,大小乘经典源源滚滚,都向中国介绍而来。经典的翻译很多,教理越来越发展,对当时做功夫的人不无影响。尤其是鸠摩罗什翻译的《法华经》、《金刚经》,影响中国之大,无与伦比,《维摩经》亦然。
东汉以后,魏晋南北朝这三百多年间,是中国文化学术,以及哲学思想最辉煌蓬勃的时期。在形而上道方面,比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还高明。不过很可惜,一般学佛的人,只懂学佛这一面,南北朝的历史未加研究,只晓得那时“清谈误国”,至于清谈了些什么,误了国没有,并没有真正了解。实际上,清谈不曾误国,倒是当国者误了文化,所以读历史不可人云亦云,要自己真作研究。
在这个时期,达摩祖师来了,当时修道证果的人很多,都是用小乘禅定的路线在修持,都是有为法门。虽然方法都对,但欠缺把有为变成无为形而上道的转节。一般大师们,如鸠摩罗什法师,虽然传了佛经,对于形而上道的翻译,也介绍得那么高深,但他修持所走的路线,还是小乘禅观的法门,也就是十念当中,念身的白骨观,或不净观这一类法门。当时,在很难追求形而上道的时候,达摩祖师来了,成为禅宗的开始。
严格来讲,禅宗是心宗,所以达摩祖师指定以《楞伽经》印心。《楞伽经》的宗旨,一句话:“佛语心为宗”。心字的问题出在这里,后来的明心见性,一切都误在这里。达摩祖师当时指出了两个方向,一个是“理入”,一个是“行入”。
理,不是普通研究道理的理,是从止观、观心的理论,进而悟道。行入包括十戒,以及菩萨的行愿,也就是在做人处事中,注意自己起心动念的一点一滴,以此证道、悟道。禅宗的宗旨,特别注重行入。但后世研究禅宗的人,有一个很大的错误,就是将禅宗指导学人轻快幽默的教授法,当成了禅。比如这个来一喝,那个来一掌,尤其以为禅宗是见花而悟道的。殊不知那都是教育法的一种偶然机用,不是禅的真正中心。真正的中心,是达摩所提出来的行入。
参公案是把古人悟道的经过,仔细研究一番,然后回转来于自己心地上体会。应该怎么走?如何才能相符?都要会之于心,二祖去见达摩祖师时,把自己膀子都砍了,他这样精诚求道的事迹,我们都晓得,但却极少有人注意到,二祖在出家以前,学问已经非常好,是个大学者。他在山东一带讲《易经》,信仰他的人很多。后来,他觉得这个学问,并不能解决宇宙人生的问题,等到再看了《般若经》后,他认为宇宙人生的真谛在佛法中,于是就出家了。
二祖出家后,在河南香山打坐八年,修了八年禅定。后世因无法获得资料,所以二祖当时修定所走的路线,是修气抑或观心,不得而知。这里要注意,修禅定八年,太不简单了,又具备了第一流的学问修养,后来又跟随了达摩祖师好几年。书上记载二祖来看达摩祖师,在雪中站了三天三夜,达摩不理,反而对他说,佛法是旷劫精勤的无上大法,在雪中站几天求法就行了吗?二祖于是把膀子给砍了下来。后世有人研究,好像觉得达摩祖师要求得很不合理,事实上,从前那一代人的宗教热忱,求法的情操,不是我们后世人所能了解的,《高僧传》中也随时可以看到。我年轻时,亲眼见人修持求法,燃指供佛,刺血写经等事实。像这种情形太多了,依现在人讲,这是愚蠢迷信,不知是我们愚还是他们愚?古今时代不同,不要轻易对古人下断语。
后来达摩祖师问二祖:你要求什么?他当时又饿又痛又冷,只说:如何是安心法门?如果是我们就会问:老师,我就是念头去不掉。二祖还远胜于我们,他已打坐了八年,再加上以前的用功,他不说念头清净不清净,问的是安心不安心,这个问题大了。
《指月录》是一部大奇书,太好了,但难读得很,要像看电视剧一样,活看。这一段描写二祖向达摩祖师求法时,达摩祖师面壁而坐,待二祖把膀子砍下来时,达摩当然拿药给他敷,包扎一番。若是绝对不理,那就不叫达摩祖师了,也不是佛法了,这中间细节没有记载。立雪、砍膀子、求安心法门的时间,并不在一起,各是一回事,书上硬是把这三件事连在一起。
安心是什么意思?安的是什么心?二祖这时膀子也砍了,又冷又饿,他的心当然不安。所以达摩祖师答他:你拿心来,我给你安!这时达摩祖师把印度人的大眼睛一瞪,一把粗胡子,一定把二祖给吓住了,这一骂,神光的魂都掉了。不是他胆子小,这个疑问太大,答案又太奇,搞得他心都掉了,魂也飞了。然后他说:觅心了不可得,找不出来。达摩祖师说:我已替你安好了,就是如此。
二祖跟了达摩祖师几年以后,达摩祖师告诉他:“外息诸缘,内心无喘,心如墙壁,可以入道。”走修证的路子,不管大乘、小乘,不管哪一宗、在家、出家,凡是修持的人,非照这几句话走不可。
“外息诸缘”,外界一切环境都要丢掉,我们学佛修证不成功,就是这一句话做不到。我们的心都是攀援心,这件事做完了,又去抓那件事,事情永远做不完,外缘也永远息不了。
“内心无喘”,就是十念中念安般法门里头,做到不呼不吸,进入四禅八定的境界。
“心如墙壁”,内外完全隔绝了,外界任何事情心都动不了,也没有妄想出现,也无妄念起来。
注意,做到这样就可以入道了,可以去证悟菩提,可以去证“道”。
达摩祖师告诉二祖这一句话,应该是在问安心法门之前的事。达摩权衡二祖的禅定功夫,再教他禅定的路线。二祖问此心不安,应该是在功夫做到了以后的事。为什么?假定一个人做到了“外息诸缘,内心无喘,心如墙壁”,敢说自己成佛了吗?心安了没有?悟道了吗?这时究竟什么是佛?什么是菩提?还是搞不清。所以此心不得安。
后来二祖传法给三祖,交付衣钵以后,比济颠还有过之,到处吃喝乱逛。像他这样大名鼎鼎的学者,出家以后专心用功,达摩祖师又付法印给他,等他交出衣钵后,晚年的生活完全不同,又喝酒,又在花街柳巷到处乱跑。人家问他:你是禅宗祖师,怎么逛道酒家去了?二祖讲了一句话“我自调心,何关汝事。”
问题来了,他求的是安心法门,达摩祖师一接引,把安心法门给他,但是到了晚年他还要去调心,此心尚不得安,可见二祖所讲禅宗安心,这个心,到底是个什么东西,仍是一个大问题。没有成佛以前,谁的心都不能安,包括罗汉、菩萨,都没有究竟安心,除了大彻大悟,谁都不能安心。
拿现在学术思想来讲,唯心思想与唯物思想,两者在争战。我们晓得心物是一元,究竟心怎么样能够造成物,如果不到成佛的境界,谁都下不了结论。所以,在理上尽管谁都会讲,事实上心却安不下来。
这就是禅宗。从此以后,禅宗事实上几乎等于没有了。
我们后世研究禅宗,都注意南宗六祖这一系,不把南北两宗连起来研究。四祖时,正是唐代要开新纪元的时候,也是玄奘法师到印度留学,快要回来的时候。那时,禅宗还没有大兴盛,仍是单传,一个人找一个徒弟,来继续挑这个担子,使法统不致断失。到了四祖以下,造就出来不少弟子,后来唐朝几个大国师,乃至华严宗、天台宗的祖师,都是由四祖这个系统下来的,比六祖系统的辈份高。
唯识、法相等经典,经由玄奘法师介绍过来后,佛法的教理更趋完备。后来的临济祖师,也是唯识宗的大师,不是光学禅的,曹洞祖师亦然。他们通达各种教理,不像现在我们一般人,不去研究经典教理,只拿个话头就自以为懂禅了。从前的大祖师们,是在三藏十二部都通彻了以后,再抛弃教理,走简截的法门,一门深入。正如孔子所讲的:“博我以文,约我以礼”,由博而约,先博学,待通达以后,再专门走一条路。
到了五祖的阶段,就是唐太宗时期,禅宗是单传,在文化上并没有占太大分量。不久,天台宗渐渐出头,当然最普遍的还是教理。接着玄奘法师回来,造成佛法之鼎盛。唐宋时候,第一流人才,第一流头脑,往往致力佛法。现在第一流的头脑和人才,都到工商业界去了。所以现在怎么会有佛法?时代完全相反了。那时学佛学禅是时髦,等于现在研究科学一样,风气使然,教理盛极一时。而领导者唐太宗,也非等闲之辈,诗好,文好,字好,武功好,佛学也好,样样好,他为玄奘法师所写的圣教序,就决非他人所能替代。
禅宗的鼎盛时期是中唐以后,晚唐到五代之间。当时佛学的理论,发展到最高峰,而六祖的禅,刚刚凑上了时代。那时唯识、法相、华严,各种佛学的理论普及于社会,差不多读过书的人,都会谈几句佛法。这时,小乘的修持已经看不上了,都走大乘的修持方法,但又找不出一个路子;于是达摩祖师所传的禅宗心印,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的法门,到了五祖、六祖时,即应运而出。
达摩祖师初传的修持方法,理论上教大家注意《楞伽经》。到五祖时改变了,因为《楞伽经》的学理太高深了,为了容易证入这个法门,改用《金刚经》。其实在四祖时已经开始了这个方法,到了五祖、六祖更盛而已。《金刚经》讲性空之理,非常简化。这时佛学的理论,似乎走到金字塔最高峰,钻不出来了,如何与身心平实地打成一体;如果立刻求证,反而成为很难的事。因为依照教理来讲,一个凡夫想要成佛,须经三大阿僧祗劫,遥遥无期,怎么修证呢?
大乘经典一流行,觉得小乘法门不足为道。而禅宗的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,更迎合了时代的需求,到了六祖时代达到了巅峰。
六祖的禅宗,从南方广东开始。那时的南方,是文化落后地区,而佛教鼎盛,原本是在中原。大国师、大法师们,都在中原地区西安、洛阳一带。六祖在落后的南方,因为用口语来传布佛法,就很容易普遍流行起来。
仔细研究《坛经》,六祖还是很注重“行”,仍是从“行”门而入。不幸的是,自从《六祖坛经》,与大珠和尚《顿悟入道要门论》等流通了以后,佛学与禅就完了。大家都晓得心即是佛,可是怎么样是“心”呢?都没有着落。所以有些人不信宗教,以为自己虽没有做好事,但对得起良心,就是佛了。至于“心”是什么?就不管了。毛病就出在这里,所以这次讲课,不包括《六祖坛经》在内,但可作为参考。
因为这个“心即是佛”的流弊,而产生了宋代理学的发达。理学家所表达的,倒是一副禅宗的姿态,是从“行”门来的禅宗,而其讲人天之道的行持,又等于佛家的律宗。唐宋以后老庄思想的道家,则等于佛家的禅宗,是解脱路线的禅宗。这三家的相互关系,极为微妙。
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的理,越说得明,佛学则越加暗淡。修证功夫越发没有着落。其实,大而无当,还不如修止观,作观心法门,还可能拿到半个果位。走小乘到底还可以求证,大乘菩提则另当别论。
再说,禅宗提倡了《金刚经》以后,因为《金刚经》讲性空,容易导致狂禅,理解上虽很容易通,但对求证则没有帮助。
禅宗的书,以《指月录》为最好,它集中了禅宗各种书籍的要点,包括了见地、修证、行愿。我在台初版《指月录》时,因销售不佳,只好论斤卖给屠宰业,用来包猪肉,这是另一段插曲。真要研究禅宗,把《指月录》搞通就够了,不过教理要熟,而且要有修证的底子,不然很多地方就看不通。
后世一提禅宗,就是参话头。其实,禅宗真正注重的是见地。比如沩仰宗的仰山禅师,被称作中国佛教的小释迦,他是晚唐、五代时人。《指月录》记载:“有梵僧从空而至,师曰:近离什处,曰:西天。”又此梵僧说:“特来东土礼文殊,却遇小释迦”,于是送了仰山禅师一些梵书(贝多叶),向仰山作礼后乘空而去。从此以后,大家就称他“小释迦”。从空而来请益的西天罗汉,不只一次,因有门人见到追问才知。
仰山跟随沩山参学时,有一天,师父问徒弟说:《涅槃经》四十卷,多少是佛说,多少是魔说?仰山说:师父啊!我看都是魔说的。沩山听了很高兴说:“已后无人奈子何。”仰山又问师父:“慧寂即一期之事,行履在什么处?”意思是我话虽说得对,此心还是不安;一期之事我是知道了,见地上我到了,境界也有一点,但是,什么是我的“行履”呢?
行履包括心理的行为,做人做事的起心动念,履字也包括功夫。沩山回答他一句名言:“只贵子眼正,不说子行履”,换句话说,只要你见地对了,不问下面的修证功夫,因为见地对了,修证一定会上路的。就怕我们见地错了,功夫再做得好,行履也是错。
因此,后世误传为禅宗注重见地,不重功夫。其实每个祖师都是见地、修证、行愿等持,差一点都不行。沩山的这句话,是天才的师父,对天才的徒弟说的,我们并不是仰山,这话对我们不一定适用。
后世学禅宗,大多是在六祖、五祖、二祖等几个前面逛一下,对后来的五大宗,诸如临济、沩仰、曹洞、云门、法眼等,都不曾研究过,这样哪能算是学禅呢?
比如临济的宗旨,讲“三玄三要”、“四料简”,这是教育法,也包括了见地、修证、行愿。临济说:“我一语中具三玄门,一玄门中具三要义”,例如“茶”一字中,具三玄门,一玄门中又有三要义,不是光讲理论。又如大慧杲一句话下面,作四十九个转语。
“四料简”,料是材料,简是选择。四料简有宾主,有方法。但古人不讲这个方法,而要靠自己去悟;如果讲明了方法,呆板的一传,大家就执著了。众生本来的执著已解脱不了,再加上方法的执著,非下地狱不可。
四料简中,什么是宾?什么是主?比如一香板打下去,啪一声,香板下面什么都没有——念头一板子空了,没有了,如果能永远保持这样就不错。用香板的方法,一语道破,那就是“吹汤见米”,知者一笑,这是骗人的玩意儿。但也不骗人,把我们的意识妄想,用一个外力截断,使我们经验到达平常所没有经验过的清净。如果以为这就是明心见性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但由这点影子也可以悟进去,这时要用般若,香板那一拍里头,透脱一悟,那叫禅。这就是临济的四料简——有时“夺人不夺境”,功夫到了清净的境界。有时“夺境不夺人”,功夫进步了一点,希望你再进一步,那个境界不是的,把它拿掉,你还是你,叫我们自己去参究。有时“人境两俱夺”,把你搞得哪一头都不是。但是,这个方法不能用,正如禅宗古德所说的,如果真提持禅宗,旁边半个人都不跟了,法堂前草深三尺,没有一个人来。
我在峨眉山曾用人境俱夺,接引过一个出家人,一脚把他踢昏了,躺在那里不动,醒来后,叩了三个头,高兴地跳起来走,从此居山顶,住茅篷去了。
也有时候“人境俱不夺”。
临济禅师并不只讲教育法,做功夫也在这里头。有时候功夫做得好,心里什么杂念也没有,清清明明,空空洞洞,那个是“夺人不夺境”。你还是你,坐在那儿,不过心里空空洞洞,这是第六意识的境界。夺人,人不动;不夺境,有一个境界。当然这境界还是会变,为什么?因为它是宾,不是主,客人不会常住的,怎么不变?这就是禅宗的秘密。但我们初步,必须让宾作主,让这个境界保留越久越好,只是不易做到。
“夺境不夺人”,这就难了。我可以大胆地说,在座没有人能做到,因为见地还没有到,所以修持、行愿也都不到。
有人问,本来清清明明的,这两天却静不下去了。我说学禅为什么不自己去参究呢?此时,夺境,境没有了;不夺人,人依然在这儿。是宾?是主?是宾中主?还是主中宾?主中主?或是宾中宾?
有时用调息,有时看光,法宝多得很,祖师们在书中都教了,不懂可以问我,高段的教法不懂,要作落草之谈,循序以进。
做气功、修定,就是让宾做主。四大不调,身体不好,气脉是宾,让身体摇摇。如果强作克制,对健康并不好;等身体调好了,宾就可以不用了,由主来做主。
念头也是如此,有时降伏不了,就念念佛,再没有办法,就唱歌吧!调心就是如此,此心难调伏的。有时功夫刚刚好一点。接下来情绪便坏得很,这时只有让宾做主了,主人家暂时搬位。
有些人学佛做功夫,充满了矛盾,气脉来了,怕执著,所以想把它空掉;气脉没有了,又想打通任督二脉。光明发现了,怕着魔;没有光明嘛,又想:怎么一片无明呢?等到空的时候,又想:我恐怕又落顽空了吧:放心,你尽管顽空,我几十年来还没有看到过能顽空的人。顽空者,顽石不灵,什么都不知道。
就这样,处处矛盾,没有办法。气脉来,干脆搞你的气脉,宾做主,没有错。气脉来时,每个部位都是痛苦的。痛就痛嘛!这是你的,是客人的,不是我的,这时我不做主,让宾做主。你越看它,这个身体就像小孩一样,“孩子看到娘,无事哭三场”,越管它,它就痛得厉害。你不管它。它就乖了,真做得到,一下就成了。可是人就是不行,气脉一来,总爱去引导它,都在色阴区宇里头转,道理都讲得很好,事情一来就统统迷糊了。
参话头是没办法中想出来的办法,那不是禅。还有“默照”,闭起眼睛,看着念头,心里很清净地坐一下,宋朝大慧杲骂这是邪禅。《楞严经》上有句话:“内守幽闲,犹为法尘分别影事。”因为没有明理,以菩提大道来讲,当然是邪禅;明了理,悟了道的人,“默照”也是禅。这是临济禅师的照用,同时是照也是用,但是一般人不知道,光是静默地守在那里,这种默照就成了邪禅。
仰山问:“如何是真佛住处?”沩山曰:“以思无思之妙,反思灵焰之无穷,思尽还源,性相常住,事理不二,真佛如如。”
仰山在这个时候,才大彻大悟,沩山可没给他一个耳光,或者踢一腿,而只是跟他讲道理。
“以思无思”,禅宗叫做参,佛教称思惟修,把理穷通透顶,到达无思之妙。这时那个能思、能觉的功能起来了,各种神通妙用,也就都起来了。
“思尽还源”,心意识思想的作用,退到那个本来去了,“性相常住”,然后性相现前,宇宙万有的现象,都摆在本位上,没有动过。“事理不二”,功夫就是理,理就是功夫,这时“真佛如如”,就同佛的境界。
仰山因为师父这几句话,他就悟了,悟后执持服勤十五年。十五年中随时随地在追问师父修行的经验,随时在求证。十五年后,再去传教,做大方丈。
为何这几句话能使仰山大彻大悟?我们自比仰山,体会看看。